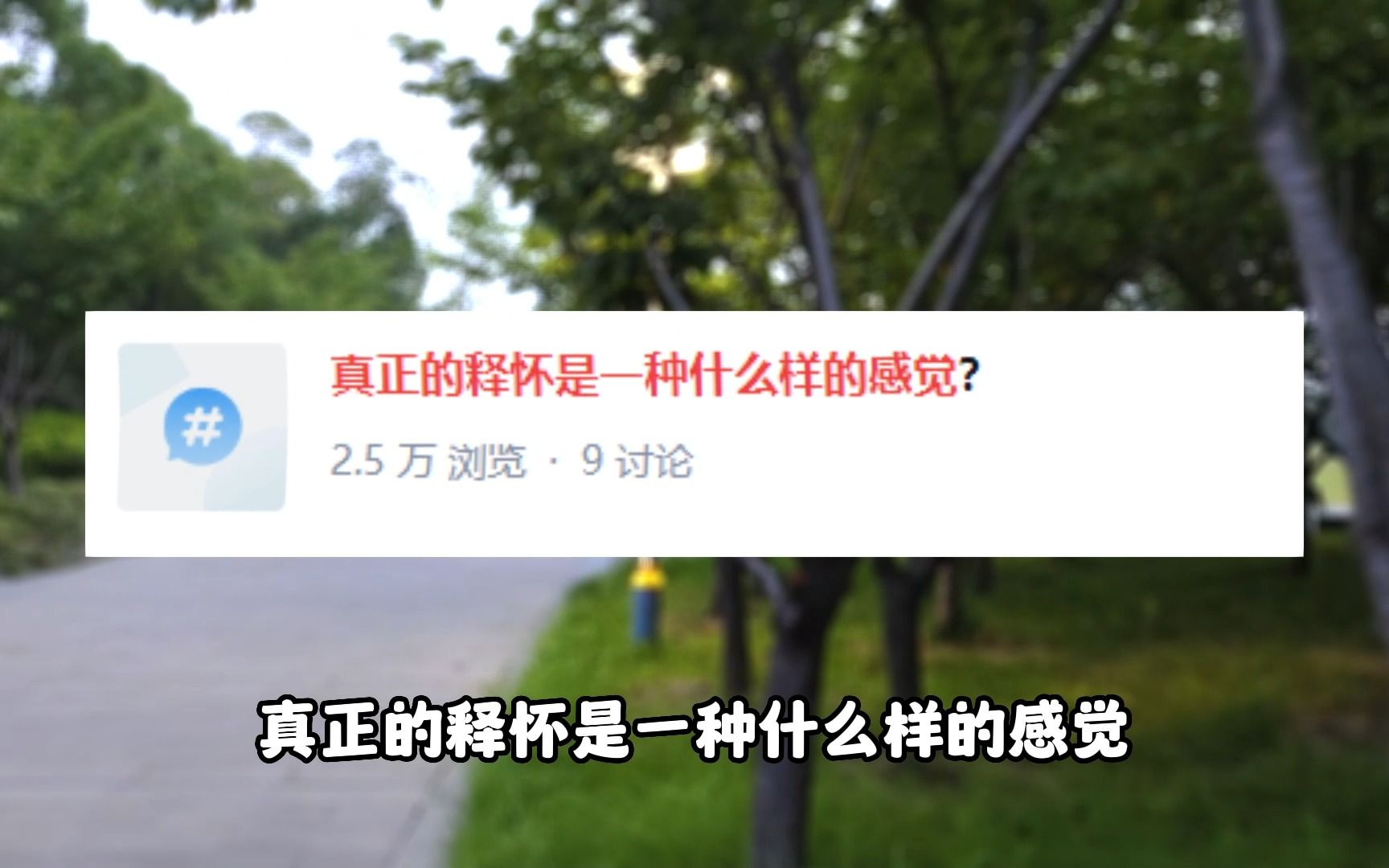苏轼士大夫精神及其启示意义
苏轼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人格典范,他为人善良幽默,为文纵横捭阖,为友可托生死,为政清正向民。诗词文赋书画全能,儒释道兼修,仁者智者合一。身处庙堂,忧国忧民,直言忠谏;谪居江湖,超然洒脱,遗世独立。在他身上所体现出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最浓最重。
一、苏轼士大夫精神的表现
苏轼作为我国古代士大夫的杰出代表,其身上所 表现出的士大夫精神有其共性的一面,如强烈的理性批判精神与积极的现实参与意识,率性的人格自由追求与深沉的悲天悯人情怀,廉正的辅君为政观念与求是的治学修身原则等,但其更具独特的个性。
(一)苏轼是一个真性情的士大夫:真诚是苏轼最为动人的本色
“少年辛苦真食蓼,老境安闲如啖蔗。”(《定惠院寓居夜偶出次韵》)苏轼从小在四川生活,经历过“食蓼”般的少年。但西蜀独特的地理环境,以及苏家任侠尚义,乐善好施的家风,特别是母亲程夫人的教导,对苏轼影响极大、极深,造就了苏轼真诚善良,
极具血性的性格。熙宁二年(1069 年),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开始实施新政。当年九月实施青苗法,熙宁三年(1070 年)改诸路更戍法,立保甲法、募役法,群臣反对。但新政之来,势如风暴,老臣反对无用,言官诤言不听,很多人因反对新法而被放外任。新法害民现象出现以后,苏轼极为不满,坚决反对以新法之名行“聚敛”之实,针对现实,特别指出:
夫兴利以聚财者,人臣之利也,非社稷之福。省费以养财者,社稷之福也,非人臣之利。以言之?民者国之本,而刑者民之贼。兴利以聚财, 必先烦刑以贼民,国本摇矣,而言利之臣,先受其赏。(《上初即位论治道二首?刑政》)
熙宁四年(1071 年),苏轼向神宗进言:“陛下生知之性,开天纵文武,不患不明,不患不勤,不患不断,但患求治太急,听言太广,进人太锐。愿镇以安静,待物之来,然后应之。”神宗为其直言所动:“卿三言,朕当熟思之。凡在馆阁,皆当为朕深思治乱,无有所隐。”苏轼谨记此言,于当年二月撰长达3400 余言的《上神宗皇帝书》:“臣之所欲言者,三言而已。愿陛下结人心,厚风俗,存化纲。”他在最后更是直谏神宗:“人皆谓陛下圣明神武,必能徙义修慝,以致太平。而近日之事,乃有文过遂非之风,此臣所以愤懑而太息不能已也。” 苏轼好友晁端彦劝他言语谨慎些,他却道:“我性不忍事,心里有话,如食中有蝇,非吐不可。”且慨然言:“使某不言,谁当言者?”苏轼非常明白这样做的后果:“某之所虑,不过恐朝廷杀我耳。”但他善良的本性,以及他本来自于西蜀田间,与老百姓血肉相连,深谙疾苦的自然禀情,使他对老百姓“有一种单纯而强烈的感情,对受苦受难的老百姓抱着情不自禁的同情心,逼得他要挺身出来,‘为民请命’”。苏轼的真诚不仅体现在政治上的直言上谏为民请命上,还表现在对待人,甚至是对待害己之人的态度上。章惇是迫害苏轼下手最为狠毒者之一,徽宗即位后,神宗遗孀、皇太后向氏摄政,大赦元祐老臣, 苏轼因此被召回朝。建中靖国元年(1101 年)三月,章惇被贬雷州,苏轼为之叹息,写信给友人黄箨(其母为章惇之胞姊):“子厚得雷,闻之惊叹弥日。海康地虽远,无瘴疠,舍弟居之一年,甚安稳。望以此开 譬太夫人也。”章惇之子章援,是苏轼元祐初贡举时所取门生,他料想苏轼此次回朝必会拜相,担心苏轼报复,便给苏轼写了封 800 余字的长信,想见苏轼一面,以观其态度。苏轼即回书一封:“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,虽中间出处稍异,交情固无所增损也。闻其高年,寄迹海隅,此怀可知。但以往者,更说何益?惟论其未然者而已。”全然不计章惇百般陷害、章援忽视师门之前嫌,仍当他们一个是多年好友、一个是得意门生,如此真诚之怀,真天下少有!“同是圆颅方趾的人,用心之不同有如此”。
(二)苏轼是一个做实事的士大夫:务实是苏轼最卓越的品格
郦波教授评价苏轼是一位典型的平民阶层的知识分子精英,特别擅长解决老百姓的实际困难和问题。苏轼中进士后,初仕凤翔签判,政务之中有一项是将终南山特产的木材“编木筏竹,东下河渭”(《凤翔到任谢执政启》),供皇家土木建造之用。当地服役“衙前”,苦不堪言,甚至到了无以为生的境地。苏轼经过深入调查,得知是官府没有将伐木放排的时间安排好,应趁渭水黄河都未涨水时放筏,因时而进退,这样费用少而危险小。于是着手修订衙规,使当地百姓可自行选择放筏运木时间,以减少危险的发生,减轻他们的负担。此方案后获准实施,“衙前之害”减轻了一半。熙宁四年(1071 年)七月,苏轼离京任杭州通判。他自来杭州后,席不暇暖,马不停蹄,奔走于所辖各县之间,察民情,体民生。他潜意识中已将自己与民众同视为“天民”,感同身受,同歌共哭。深入民间,务实求真的品格与作风,使他看到了饿殍满地,哀鸿遍野,公堂鞭扑,民不聊生的一幅幅惨象。
吴中田妇叹
今年粳稻熟苦迟,庶见霜风来几时。
霜风来时雨如泻,杷头出菌镰生衣。
眼枯泪尽雨不尽,忍见黄穗卧青泥。
茅苫一月垅上宿,天晴获稻随车归。
汗流肩赪载入市,价贱乞与如糠粞。
卖牛纳税拆屋炊,虑浅不及明年饥。
官今要钱不要米,西北万里招羌儿。
龚黄满朝人更苦,不如却作河伯妇!
自觉为民代言是苏轼作为士大夫发自本能的良知,为苦难民众呼号的诗篇,利如匕首,是他常遭时忌的重要原因之一。熙宁十年(1077 年)四月,苏轼徐州上任,不到两个月遇黄河决口,时又大雨,徐州城下水势急涨,情形危急。苏轼亲率吏民及守城兵卒,修筑长堤,抗击洪水。自堤开工之后,苏轼日夜巡视,派官吏分头守城,晚上就睡在城上,历时 70 余天,终获成功。喜作《河复》诗,序曰:“乃作《河复》诗,歌之道路,以致民愿而迎神休,盖守土之志也。”为消除水患,求徐州永久之安宁,他实地勘察,上书朝廷,请修河堤。“改筑外小城,创建木岸四条,大坑十五处,尽加堵塞。”[1]237 并在子城东门之上建“黄楼”,刻自撰《奖谕敕记》一文及皇上诏书,以示纪念。后又遇天降大雪,徐州出现燃料危机。他四处寻找,终在徐州城西南的白土镇寻得“石炭”(煤),以此开启了徐州 1000 多年的煤炭开采历史。
元祐四年(1089 年),苏轼除龙图阁学士知杭州。他储粮防灾,开设病坊(取名“安乐”,这是较早由官府设置的民间医院),施药(“圣散子”)防疫。治六井,解决杭州居民饮水问题。开西湖,不仅为杭州提供了稳定清洁的水源,而且消除了陈年水患。苏轼两次在杭为官,为百姓做了很多实事、好事,杭州的百姓也十分爱戴这位务实清正的好官。当年苏轼被贬黄州时,杭州民众为他设解厄道场,祈求上天保佑他能消灾平安。苏轼也曾说:“江山故国,所至如归,父老遗民,与臣相问。”(《<杭州谢上表二首>之二》)。
(三)苏轼是一个有气节的士大夫:惜节是苏轼最可贵的个性
苏轼天生是一个率性任情的人,在虚伪而狡诈的官僚社会里,他自然成了与世俗格格不入的“狂者”。他自己很明白,如他诗中所言“我本不违世,而世与我殊。拙于林间鸠,懒于冰底鱼。人皆笑其狂,子独怜其愚”(《送岑著作》)。王安石变法之时,苏轼是反对派中的少壮分子,言论最为激烈。“乌台诗案”后,他被朝廷重新启用,同时一批旧臣也被重用,如吕公著、司马光等人,“元祐更化”拉开序幕。元祐二年(1087 年),司马光上书罢废免役法,苏轼凭他在地方为政的实际经验和体会,认为免役法确是比差役法进步许多的良法,便贾勇两次往见司马光,据理力争,但终因司马光固执己见而失败。苏轼本已受过一次重大打击,刚刚从被贬之地黄州召回朝,立足未稳,便如此仗义执言,实为少见。由此推知,他后来又遭元祐朔党攻击终是迟早之事。苏轼读书求知,原本就是期望能以自己的才智,解百
姓之苦难,救朝局之孤危。因此,他对因自己直谏诤言而遭打击陷害毫不在意。危身奉上,本又是文人儒者应有的节操,奋不顾身地谏言上策,是他赤子之心的真实表现。作为一名士大夫,苏轼文人气质偏浓,而官僚习气全无,在重名利、弄权术的官僚社会,能惜身自好,“遗世独立”,是其所是,非其所非,绝不妥协,用激烈的文字语言涤荡一切邪恶,实属难能可贵!苏轼在《次韵周邠寄雁荡山图》一诗中说:“西湖三载与君同,马入尘埃鹤和笼。”跻身官府群僚之中,他的精神却十分地孤独。“独鹤不须惊夜旦,群乌未可辨雄雌。”(《和刘道原见寄》),虽是对好友刘恕的向往,但也反映出“群乌”之中苏轼心头无边的寂寞。“我本麋鹿性,谅非伏辕姿。不如汗血马,作驹已权奇。……君看立仗马,不敢鸣且窥。调习困鞭箠,仅存骨与皮。人生各有志,此论我久持”(《次韵孔文仲推官见赠》)。他生性只是一只奔游于原野的麋鹿,如今却做了一匹“立仗马”——那种披红挂彩、金勒雕鞍的仪仗队里的马匹。“终日无声,而饮三品刍豆;一鸣,则黜之矣。”(《新唐书?奸臣传上?李
林甫传》)他满心厌恶,百不自在。对那些沉浮利禄的无知下士,沐猴而冠,俨然作态,充满了卑视与厌憎。有老者章传道劝他,稍稍贬抑一点自己,以适应这个现实,苏轼昂然答道:“如尔自贬,终不谐俗,故不为也!”
在宋代士大夫阶层社会中,家养伎乐,歌舞侍宴的风气盛行,苏轼家也不能免俗。他喜欢与朋友在一起群居热闹,但从不昵妇人,也很少与家中侍女说话。 苏轼的家伎主要是用来招待那些不可与言而又不得不招待的俗客,以丝竹歌舞来应付乏味。真正高朋嘉宾,则只需香茗佳酿,相坐欢言,兴会无前。“已将镜镊投诸地,喜见苍颜白发新。历数三朝轩冕客,色声谁是独完人”(《书寄韵》)。50 岁后的苏轼对自己一生不耽声色也颇感自豪。有人说苏轼如此是为养生,这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惜身自律的品性修养。
二、苏轼士大夫精神的当代启示意义
宋代文化是一种高度成熟的理性文化,苏轼作为宋文化的集大成者[3],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,宋代士大夫的楷模,其影响深远,是自宋以后的历代士大夫所希望能做到的景仰对象,他身上所体现出的士大夫精神于当世也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。
(一)在为政层面上,苏轼廉政为民的思想仍具有当代的启示意义
当代中国的廉政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,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,并结合当代中国的国情、党情丰富和发展而成的。苏轼廉政为民的思想是中国古代传统廉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《人民日报》社课官的领导观,使他从政 40 年,历任八州太守,三部尚书,而他的政敌从未能在廉洁问题上对他有任何的诘难,以致谢景温借苏轼兄弟乘船运送父亲棺材回乡,诬告他们滥用官家卫兵一事沦为自取其辱的笑谈。他作为一名清官,平时俸禄,“随手辄尽”(《与章子厚书》)。出任密州太守时,竟到了吃顿饱饭都没钱的地步,拉着好友密州通判刘廷式到城墙根挖野菜吃。被贬黄州时,更是不名一文,生计极其困难,只得躬耕东坡养家糊口。苏轼“功废于贪,行成于廉”(《六事廉为本赋》)这句话已成为无数为官从政者的座佑铭,他的廉政为民的思想与实践,深刻地启示着党政领导干部要崇廉拒腐,以廉为首,以民为本,勤政为民。“以其功兴而民劳,与之同劳;功成而民乐,与之同乐,如是而已矣。”(《既醉备五福论》)尚若如此,则定能做到不忘初心使命,风清而气正,“不想腐”才有了真正的思想根基。
(二)在社会层面上,苏轼求真向善的精神仍具有当代的启示意义
有学者认为,“中国正在逐步形成一个对社会起主导作用的精英阶层,这个精英阶层在当代社会的政治领域、社会领域、文化领域,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”但这一精英群体不能通过人格力量、道德表率而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。究其原因,大多是因迷失心智,失去良知而“失心”“失语”。苏轼无论从哪方面来衡量,他都是当时社会上当之无愧的最杰出的精英分子。他既执着于自己的入世愿望,又能身心自在,心境平和。24 岁时,在《送宋君用游辇下》诗中,苏轼鼓励他的朋友:“赖尔溪中物,虽困有远游。不似沼沚间,四合狱万鲰。纵知有江湖,绵绵隔山丘。人生岂异此,穷达皆自由。”实际上,他也是在明示自己,读书为求世之用,要在更广阔的天地展示才能,发挥光热。苏轼毫不掩饰对政治权力的渴望,对政治抱有无比的热忱与信心,因为他认为现实政治的权力,具有广泛的改变一切的力量,可以实现他为生民的福祉做一番事业的理想。但当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时,他又坦然面对,乐观对待,唯一不变的是赤子之初心,唯一能做的是求真向善,敢说真话,敢做实事。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,当时对茶、盐、酒、矾实行官卖,称之为“官榷”。当大多数官僚以此盘剥百姓,中饱私囊时,苏轼却于元丰八年(1085 年)上《乞罢登莱榷盐状》,请求朝廷罢除登、莱两州榷盐。后又作《上韩魏公论场务书》,向宰相韩琦提出“以官榷与民”的主张。既坚持操守,又能想方设法为百姓做好事,做实事,“苏轼受到后世士大夫的普遍热评论部所编录的《用典》一书中,总书记引用苏轼的名句达 7 次之多[4]。苏轼超然物外的名利观、以人为本的惠民观、节用廉取的律已观、建章爱,实为历史的必然。”[6]
苏轼求真向善之举不可胜数,在黄州施救溺婴,
在儋州办堂教学,在常州退宅于妇,等等。他深刻启示着社会精英们应不趋炎附势,不违背良知,敢说真话,善行好事,以期以自己独有的人格魅力开启良好的社会风尚,而成为千古垂范的传播正能量楷模。
(三)在文学层面上,苏轼旗帜引领的精神仍具有当代的启示意义
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,也是传播文化的主要媒介。同时,文学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文学的繁荣也有利于文化的发展,而文化的发展又为文学创作提供更多的源泉和更广阔的背景。2021 年 12 月 14日,总书记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、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:“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
艺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,需要在党的领导下,广泛团结凝聚爱国奉献的文艺工作者,培养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的文学家、艺术家。”苏轼作为北宋中期的文坛盟主,他甘为人梯,奖掖后进,将宋代文学推向高潮。在欧阳修主盟宋初文坛时,他就明确表示把将来领导文坛的责任交给年轻的苏轼,并预言苏轼成就会超过自己。苏轼当仁不让,他对门人宣称:“方今太平盛世,文士辈出,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。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,故不敢不勉。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,亦如文忠之付授也。”(李廌《师友谈记》)苏轼高擎宋代文学革新运动大旗,沿着欧阳修开创出的道路,继续前行,发扬光大。他强调“文以载道”,要关注国家社会,这使得宋代的诗文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刚健的风骨。“开口揽时事,议论争煌煌。”(欧阳修《镇阳读书》)苏轼好论,他的亭台游记文赋几乎篇篇有议论,在诗中也大量使用议论。过多议论虽会削弱诗的韵味和意境,但也为诗歌开辟了新的题材范围和美学意境。这种诗歌创作的形式虽不是苏轼一人所为,但他的哲理诗无疑影响着宋代讲坛一大批的后进诗人,使宋诗呈现出与唐诗完全不同的风貌。苏轼在词的创作上所取得的非凡成就,就其贡献而言远超于苏诗和苏文。他提出词“自是一家”的创作主张,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放之词,开豪放词派之先锋,使词冲破“艳科”的樊篱,成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,从而在宋代达到巅峰状态。在苏轼的门生中,无论是“苏门四学士”还是“苏门六君子”,他们的文学成就不同,各有风格,苏轼从不强人与他同调,十分尊重他们的创作,因而在当时形成了各自的文风,创造了宋代文学各具特色,万象纷呈的新境界。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品。苏轼甘当旗手,敢于引领的文坛盟主气质深刻地启示着当代的文学家、艺术家要深入实际,关注社会,守正创新,为时代立言,为人民创作,推动文化强国建设不断向前发展。
三、结束语
苏轼,这位一谈到他“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暖地会心一笑”的大文豪[7],“达则金马玉堂为帝王的师傅,开封州郡为封疆大吏;穷则为大廋岭外的南荒逐客,桄榔林中食芋饮水的诗人”。他真正做到了“穷不失义,达不离道”(《孟子?尽心章句上》)。研究东坡文化、讨论东坡精神已成为一门学问——“苏学”。其实无论是“东坡文化”还是“东坡精神”,其核心要义仍是士大夫文化和士大夫精神。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,是当代文化建设,乃至文化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。苏轼作为文化先贤和士大夫楷模,他的事迹和文学作品中蕴含着极其深邃的思想和令人景仰的精神,激励着后世的士大夫们“铁肩担道义,妙手著文章”,不惮前驱。而这一切亦超越时空,在当代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启示意义。这或许才是讨
论、挖掘“东坡文化”和“东坡精神”的真正意义和终极目标。
——程朝晖